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
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正弟:
我以至悲痛、至恳切的心情给你写这封信。
你还记得前年我回家的时候吗?有一回,在去上海的火车里,我给你看“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同时对你发了一通议论,后来,你疑心地问我:“你这种看法会不会犯错误?”当时,我很不以为意,然而,不料,时间不到一年,你的话竟应验了。
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了解怎么一回事了。我成了一个右派了。而且由于我的地位较高,影响较大,理论涉及的面较广,较深,“情节”不能不算是比较严重的。
你感到惊奇吧!我也曾是惊奇的,但是现在不了。我的犯错误是有深刻社会根源(家庭出身、学校教育、职业环境)和思想根源的。而且,你可能也已理会到,在这一次出现的右派分子中,历史好、表现好、工作好,“政治好”如我者,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当然大多数并没有登在报上)。我曾以为自己是一种例外,现在知道得多了,才知道并非例外,并不奇怪。
我比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反面的教员”,充分利用这株“毒草”来做肥料,对我的斗争曾进行了近两个月。我已经坚决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本来在这封信里不应该再说许多似乎为自己辩护的话,还多说这么几句,不过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哥哥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右派,是一什么样的人。
虽然你没有像我这样的政治经历,但是也许也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的人在犯错误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尽管有这种错误的出人意表的严重性质,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我是不会逃避错误的。只要需要的话,我甘愿让革命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向群众承认了一切错误,并且做了检讨。这些是被认为是好的,但是,尽管如此,党是大公无私的,它的纪律是铁的,处理还得严肃处理,我要痛苦地告诉你,我不但已被撤销领导职务,而且已被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我也要告诉你,尽管我“触了这样大的霉头”,却并不是由于私怨,有什么仇人要整我,相反,领导上倒一直是关心我的,包括总理在内。然而党纪无私,我自己在白纸上写了黑字,砍也是砍不掉的。纵然有人想“救”我一把,也是没有办法的,“救”我的办法,现在只能是斗争我,处分我。但是,我知道,党会继续关怀我,只要我在今后的考验中表明确能改正错误,我就一定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誉和地位,并且继续前进。
这件事情,我瞒了家里快半年,现在至少必须对你说清楚。我的最后处理,不日即将做出,开除党籍,降个三四级,都是必然的。应我唯一的要求,是去农村参加劳动。这一点愿望,社长最近同我谈话表示,大致可以实现,我的事情,我不能再不告诉你们了。
想来想去,这件事件必须要告诉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父母亲知道,也不能让芍姊、小姊知道。至于应当不应当让侬姊知道,我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我想总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我要请你决定,但是就是你决定要告诉她,也必须先写信征得我的同意。
这件事情对我个人的物质生活与家庭生活无疑是有影响的,例如薪水收入就要减少几十元,但是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张贻已经证明是一个党在政治上的好同志,也是我在困难中的好妻子,几个月来,她表现了惊人的刚强与忍耐,处理了这样一个于她来说也是极其难堪极其矛盾的问题。她总是支持我而不包庇我,批评我而不疏远我,她负担着自己的、全家的以至我的感情重担,而表现得完全若无其事,我真是感激她到极点。
下面一个关于家庭的问题是以后三四年,我可能不会回家了。父母年纪大了,我这几年心里有打算,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是应当尽到儿子的职分的,然而现在,背负着这样重大的包袱,在得到机会把它卸下来以前,我是不会想回家的。正弟,我不是一个孝子,但是父亲从小教育我的封建感情,到现在还是强烈的,想到这个问题,我每每会泪下。但是,我现在宁愿负寡情不孝之名,而不愿在我摘掉帽子之前回家,带回我的恶名来增加他们的羞辱。
正弟,多少年来,都是你代替我担负着对家庭的责任。解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看到天下太平,我原来想,除了工作关系不能承欢膝下而外,其他方面是可以期望尽到儿子的职分了,然而不料,不自检点,居然出了这样简直不可思议的大毛病。写到这里,我的心里像绞一样的难过,然而,我又不能不再一次把责任推委到你和三位姊姊的身上。正弟,我不敢要求你原谅我,饶恕我,但是,我要请求你可怜我的不得已。
正弟,你一定关心我的前途。我曾是情况知道得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切都按照政策办事,我是彻底地被孤立了。每天我都一个人坐在我那空落落的大办公室里,看报,读书,写反省笔记,写思想汇报,除了参加一些极少的、人人都参加的会议而外,是绝对地不与人来往。只除了张贻,不过她是一个大忙人,一天要开好几个会,累得精疲力竭,同时她也应当同我“划清界限”,因此,就是我们也谈得不多。实在闷得发慌的时候,我就到城外去散步。你还记得那粪场旁的天宁寺宝塔吗?你以为很远吧,我现在随便一走就可以走到那个地方呢!
至于前途,处理是定了,就向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就世俗的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很宽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简直照样吃饭穿衣,没有什么(也正因此,可以完全不必告诉父母)。但是,就精神的意义上说,帽子要长期地戴在头上,要继续保持目前众人对我、我对众人的关系。而且,也不能不提到一个现实情况,这几年我实在是一个受宠过甚、踌躇满志的人,突然从云霄掉到深渊,从狂热之际归于冱寒,从自认满怀忠心而被认为叛逆,这个痛苦,我不能向你诉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这样的痛苦。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正弟:我现在想谈一谈,我的问题对你的意义。
我相信,我的问题一定会引起你的震动,让你震动吧,震动得越强烈就越好。
你应当从我的问题得出深刻的教训,毕生的教训。你应当明确地看到,你的思想几乎是完全没有经过改造的,你出问题、出危险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你不妨把你的哥哥看成是代你受惩罚的一人,如果你不希望他再翻第二次跟斗(一个人短短的一生,这样的跟斗是经不起几次好翻的),你也就要立志不再陷他的覆辙。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做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但是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但愿我的教训能够深深地刺痛你,让你能发愤补上这一课。正弟,市面上出版了不少反右的小册子、大册子,我劝你务必不要爱惜钱,统统去买来,好好地精读,一字一句地读他两遍三遍,拿来同自己平素的想法对照一下,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后一言一动好心里长存警惕。另外,我劝你,把你的“江南园林”放一放吧!到图书馆去把去年四月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好好地读一遍。花它个把月时间,如果你这辈子能免于遭受我已经受了半年,还要继续受几年的痛苦,这是十分值得的。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吧!这是第一件我希望于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你不能再做“梁上君子”了。无论如何,要立刻参加工作。否则太危险了。许多像你这样生活着的人都出了毛病。你上次来信谈到就业问题,我在复信中劝你立刻找到工作,但是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告诉你也就没有说穿,现在,我代你拿主意,立刻进民用设计院去罢!不要再犹豫了。老老实实受一个组织的管束,什么个人志趣,个人事业,先抛开一旁,等到组织上同意你做的时候再做吧!脱离了组织,脱离了群众,脱离了革命的气氛,受不到教育,暂时也许会“免于一难”,但是终究要摔大跟斗。我虽然在组织中,但是这几年实在也是走顺风,太得意,太浮了,自以为一切都看穿,看通、看透了,然而结果竟摔了如此惨绝的大跟斗。你看看我的榜样,下定决心吧!
正弟:如果你看了我的信感到痛,那就痛吧!我只怕你不痛,我希望我的信会狠狠地刺痛你。如果你看了我的信,会感到吃不下饭去,会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像我一样不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那么,我只会感到,我的痛苦多少有一部分移植到了你的身上,是给你打了防疫针生了免疫力。正弟,我不会愿意你痛苦,然而,这一次我却不希望你轻心地寻常地看待这样一件事情呢!
也许要几年以后才能再见了,我希望那时我能以不辱没我们家庭的荣誉的一员的身份与大家相见。白李这几年的教育是要拜托你了,希望你把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严格地要求她吧!
慎之
(1958年)二月十二日
这是李慎之先生被打成“右派”后写给胞弟的一封信。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等职;平反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这封信原件近7000字。从内容可知,“反右”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关。这一报告曾导致了一连串的反应,先在波匈,后在中国。这一震荡以“鸣放”开始,以“反右”告终,殃及大批知识分子的命运。党外党内,“不是一两个,而是整整一大批”。
作为案例,李慎之先生早年的这封信,显示了“思想改造”的功效。一个人同时是审判者和异端、告密者和嫌疑人等等诸般角色,这种痛苦,诚如作者所言:“并不知道有任何艺术作品曾表现过”;尤其是党内知识分子,要承受正直与忠诚的双重煎熬。其结果是,它成功地剥夺了一个人的正义感和身份感:“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读李先生信,满纸荒唐,恍若隔世。回过头看,“思想改造”却如沙上建塔。当“旧思想”灭绝、“新思想”破产,在一片喧嚣与骚动的后面,我们听到的是寂然无声的荒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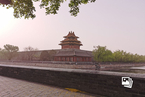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