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
我们从广州回北美两周了。在中国这两个星期,奔波折腾居然没有生病。一回来,先是儿子感冒,然后传给我。我打电话告诉广州的朋友,她说,你水土不服呢。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我是不服中国的水土,还是不服美国的水土。
这次回国本来是专为陪82岁的母亲到广州开画展,带着不懂中文的儿子。所有这些成人的活动都和他无关,总得给他安排个对中国有好印象的节目吧!就专门坐了飞机上京来爬长城,兼顾着骚扰你一下。
因为我离开中国时间太长,根本没想到五一节整个一周是全国劳动人民放大假的日子,更没有想到老乡们现在都能出远门旅游。选了这么个日子爬长城,脚跟踩脚跟,臭汗熏臭汗,给他留下的印象不谓不深刻。
那天你18岁的儿子带着我8岁的儿子上长城,8岁的刚得了两把仿古的中国兵器,舞得不亦乐乎,恨不得把长城顶上的拥拥人头扫平;18岁的忧心忡忡地跟着那随时惹祸的刀尖转,一步不离。我这边吆喝不住8岁的,只好对18岁的说,男孩子就爱玩刀枪,你小时候也玩刀弄枪吧?他说,他小时候没得玩,爸爸生病,妈妈顾不上,而且从小学起学习一直就紧张。
看着你老成持重的儿子,我又不平衡了:十年后的亮亮如果能像他这么懂事,我不就该念阿弥陀佛了?可是那孩子懂事的代价让当妈的多心疼呢。
其实,我们成人的操心和安排常常是先入为主,孩子们有自己的眼睛和脑筋,走到哪里,看见什么,都能转换出智能。我们到广州那天,一出白云机场,亮亮就自言自语道:“这污染也没有那么厉害嘛!”到我父母家,他上完厕所冲出来叫道:“他们用的是美国马桶!”我喝住他说:“马桶就是马桶,什么美国马桶中国马桶的!” 我心想,这小鬼老气横秋地在唠叨什么?
几天后,他说想看米是怎么长出来的,我就带他到我当年插队的广东农村去。这是珠江三角洲上的一个富裕农村,一个村有两万多人口,一年两季种水稻,春插夏收,夏插秋收,还加一季冬小麦,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我16岁到那里插队,待了三年。
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三十年后回去,居然看不到一块稻田。村子还是那村子,青砖大瓦房拥挤着的窄巷还是那么窄,那么脏。地上乱跑的猪没有了,狗没有了,几只母鸡嗑嗑地找食。人还是那些人,当年我的生产队长就坐在当年队部门口的青石上和几个老头磕牙。队部旁边,他当年给我和另一个女知青隔出来的小屋拆了,他在男厕所旁边为我们搭出来的厨房也没有了,他肯定也忘记怎么把我们的800元安家费(相当于现在的8万了吧?)派了什么更好的用场。
可我还是告诉我儿子,我的卧室(用“卧室”这个词显然像是黑色幽默)因为没有窗户,晚上不得不把门打开来睡觉。早上开门进厨房,一夜从隔壁男厕所钻过来的蟑螂和老鼠就飞也似地四散逃去,在锅台和锅里留下一颗颗粪便。我还带儿子去看村边的一条白沙河,我们队在上游,河边有一个埠头,埠上有一棵大大的水蓊树。每天早上各家女子到埠头洗衣挑水,是乡村生活最美丽活泼的一景。只是我们走到河边,看见快干涸的河床上流着混浊的泥水,埠头已经倒塌废弃,只有那棵大水蓊依然生机勃勃。
我们往村子外面走,看见一栋栋三层小楼和一座座厂房,当年我们刨红薯摘绿豆的光头岭,变成了一个四百亩地的大花园。山顶种的是花草,山腰还保留了荔枝果木,山下是一座现代化的制衣工厂,五栋崭新的厂房和三栋宿舍连着花园。工厂主竟然是当年和我一起下田干活的小妹一家人。小妹和她的丈夫在客厅(那可是真的客厅!)里悠闲地和我聊天,工厂的事务由儿女分管,主管是小儿子,我离开乡下那年,他还是个流着鼻涕没有穿裤子的娃娃。
我领着儿子走出村,好像走出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切都让人难以置信。在回程的路上,我对儿子说,没有看见米是怎么长出来的,但是你看到一个农业国家怎么走向工业化,这可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见的。他若有所思一阵,然后说,“我们有个老师从中国旅游回来,给我们看幻灯片,她说中国的天空都是灰的,看不见太阳;厕所没有马桶,只有地上一个洞。”
我这才明白为何他前几天有那样的自言自语。
地上一个洞的厕所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只不过那是二十多年前在中国农村发生的事实。还有一个关于中国城市的厕所的事实,也让我一生难忘。
我六岁那年被幼儿园园长带着去考一所名校,记得快轮到我的时候忽然想上厕所,而厕所又在巨大的操场的另一头。园长让我忍着,我就忍了,结果一考完出来就尿了裤子。回家的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一路难受。更没有想到,以后的五年,在这条来回三个小时的漫长的路上,我经常忍受没有厕所的痛苦。那时候的孩子真是很皮实,也不怕坏人拐骗,而现在我8岁的儿子自己走过两条街去学校,就会招来警察和非议,据说现在中国的孩子上学也都是由大人接送了。
如果仅仅是没有厕所而常要忍尿,也许如今我已忘记,因为人的记忆偏偏有选择光明的偏向。但是很快“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烧进小学校园,有一天中午午休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忽然发难,说我的父亲是牛鬼蛇神,我也就不配再当班长,连上学坐公共汽车都不敢坐座位,怕被人发现成份不好而赶起来,回学校随时会被同学批判——我可是小学生呀!我家住在大学校园里,父母被关在变成牛栏的教室里,他们的学生会把我拦在路上,要我喊打倒父母的口号。
因为我“被打倒”,有点架子的同学都不屑与我交往,尤其我们班,大多出身干部家庭,都比较敏感和清高。有一阵我唯一的朋友是班上没人理的“虱子头”。这个女孩子长一头发黄的蓬发,像狮子,后来又长了很多虱子,于是“虱子头”和“狮子头”双拥。
我坐在她旁边,常看见黑色的虱子在她的蓬发间出入,她的虱子居然不往我头上跳,恐怕也是讲“阶级阵线”,分明比虱子主人的政治觉悟要高。她成份好,老师让她和我坐,又要我帮她的功课,家庭小组也要到她家去上。后来“狮子头”调班,我又被安插到另外一个成份好家里穷的同学家上家庭小组。她家一进门就是一张大床,一家六七口人,所有的活动都在从床到门口的几块方砖之间,而她还有一个从农村倒流回城的姐姐,坐在床的另一头观赏我们的学习,很拥挤,也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嫌弃我这“狗崽子”。
再后来,班级拆散重组,造船厂和远洋公司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可能是航海和造船让人心怀宽阔,他们的孩子不计较出身,我便被接纳,放学后常常去她们的家去玩,再花一两个小时自己走路回家。他们都住在不通公共汽车的郊区,我却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常去常往。当时不懂,现在想来是怕被孤立,和现在美国孩子的孤独、中国独生子女的孤独却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这就是我上小学几年的经验,真显得一无可取。但事实上也不尽然。
老师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从旧社会教书教过来的苏宝珠。她教几何和珠算,不仅使我爱上了数学,还让我从“狗崽子”的自卑里抬起头。具体她做了什么?无非就是没有把我当“异类”。五年级转学到干校去,对学校毫无留恋,唯一舍不得的是这位老师。许多年我都记得她,曾认为她早已作古,当年她是老师中年纪最大的。这次小学同学说她还在世,我竟吓一跳。想来想去,最后不敢去看她,不敢冒险把对她的印象变得滑稽或伤感。
这么复杂的往事,怎么给一个第一次来中国、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8岁孩子讲明白?中国,是在我们这次回国前一个月才开始以历史和地理的概念进入他的知识库存。他们学校每学期都有三个外国文化周,每周专门介绍某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因为中国的历史太长久内容太多,中国周持续了两周。他每天回家都和我讨论当天学到的内容。比如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三岁登基的,而最早的一个皇帝杀了很多人;中国有些什么古代发明,中国的文字有什么特点,等等。上面这位老师的旅游介绍,也是其中的一节。她给23个美国孩子留下关于现代中国一种片面的印象,只有其中一个孩子马上有机会得到纠正和补充,另外的22个或许永远不会有机会纠正。
教育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亦传播偏见。我在中国的网谈上看到中国年青一代对美国的偏见,明显也是被灌输教育出来的。。差异构成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距离,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隔阂。
其实,这种不可思议的差异,天天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今天我到商店里去买种花的肥料,亮亮不知道从哪里捧出一盒萤火虫蛋,要买回去放到院子里。他把我拖到一个大冰箱前,里面居然有蚯蚓、螳螂、花大姐、小田螺……等等的蛋。我告诉他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整个夏天都在草丛里抓螳螂和蚂蚱,到果园里偷水果,鱼塘里偷鱼。他非常羡慕,问我有没有被抓过,我却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夜已深,就写到这里吧!早已不去想那些往事了,回一次国就又“陷”进去了。真叫作不可救药!

“三十年后回去,看不到一块稻田”
2006年06月12日 00:00
偏见和成见,先入为主的观念,处处为教育下一代设下了陷阱
版面编辑:运维组
图片推荐
编辑推荐
- 能源 | 【特稿】为何换表后费用大涨?
- 金融 | 范一飞案一审开庭 受贿3.86亿元
- 科技 | 华为P70系列如何搅动市场?
- 财新周刊 | 黄金因何暴涨
- 封面报道 | ①阿里退守 ②大厂在收缩
最新文章
- 20:36中国野保协会与旧金山动物园开展大熊猫国...
- 19:30人事观察|交流干部许永锞履新广西常务副主席
- 18:17村镇银行改革化险持续推进 多家村镇银行...
- 17:02打通束缚“科技型国企”新质生产力发展 ...
- 15:08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期盼对中国公民的免...
- 12:34一波数折 吉林四平特等劳模郑小东案再审开庭
- 11:56极氪CEO称将聚焦纯电 没有增程式车型计划
- 08:38中证监发布五项资本市场对港合作措施 E...
- 08:34中核钛白“定增+融券”套利违规 中信、...
- 08:30被立案调查半年 高瓴QFII基金拟购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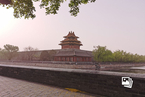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